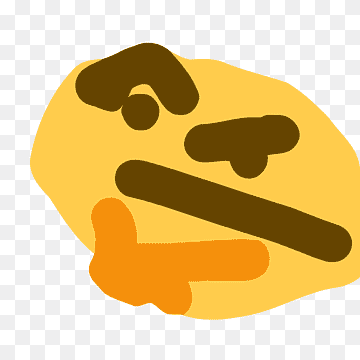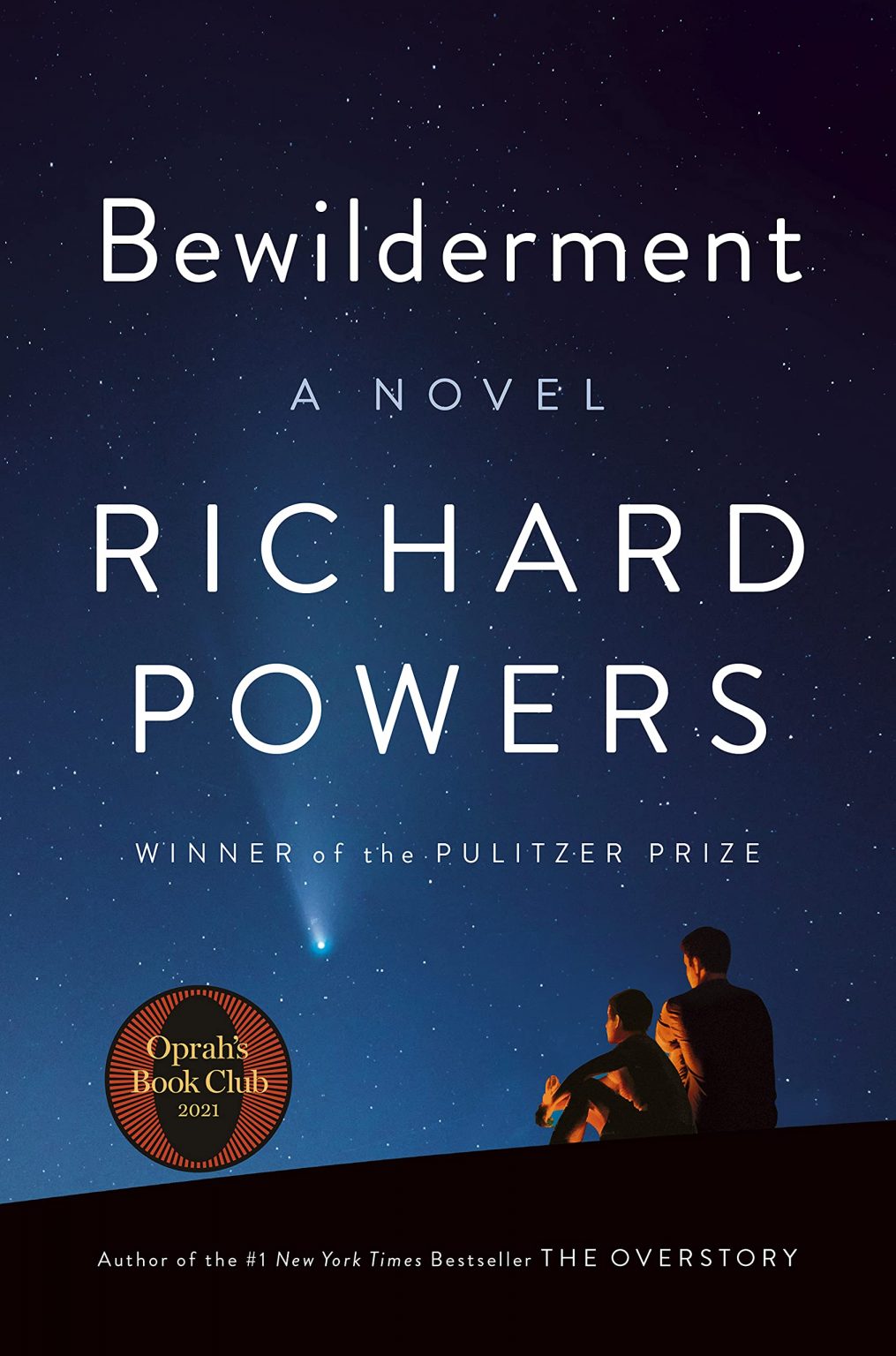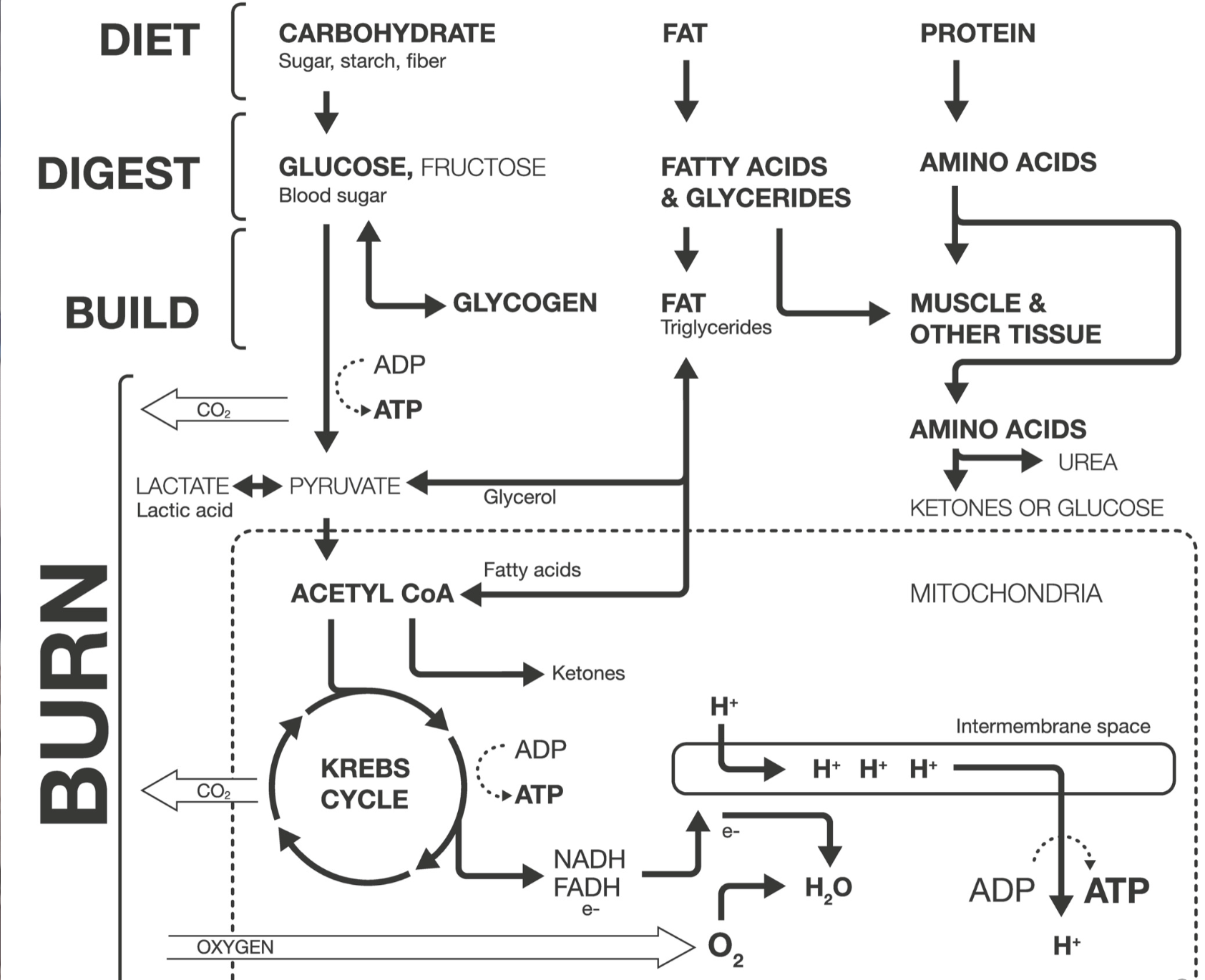This book is beautifully written, with an exceptional command of language. Every sentence is precise and purposeful, with no excess or unnecessary words. Reading it feels like watching a highly skilled surgeon perform a difficult operation—swift, precise, and masterful. The author’s ability to convey deeply moving emotions through straightforward, almost clinical narration is remarkable.
The depiction of familial relationships, in particular, is profoundly touching. My impression is that the author excels not just at writing about people, but at understanding them. He possesses a sharp sensitivity to human emotions and self-respect, yet he carefully conceals these piercing observations beneath calm, unassuming prose. Even the most tranquil words can carry undercurrents of emotion, waiting silently before striking the reader’s heart at just the right moment. It’s also possible that the author’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upbringing have shaped his deep reflections on life and death. Every time I read one of these steady yet weighty passages, I find myself holding my breath for a few seconds—feeling a mix of sorrow, and at times, a quiet realization of my own naivety and fragility.
That said, there were parts of the book that made me uncomfortable—particularly when the author discussed his mother and his role as head of the household. Part of this discomfort stemmed from his distinctly male perspective, and part from the patriarchal norms that are so ingrained in Minnan culture. There were other moments that I found unsettling while reading, though I can’t quite recall them now, so I won’t dwell on them here.
In the final afterword, the author writes:
“People are different, and that is a kind of luck—for it is these distinct individuals who shape the rich and varied world we experience. But at our core, we are all the same, and that too is a kind of luck—because if we are willing, we can find the common threads that allow us to truly see one another, reflect one another, and warm each other.”
“This is what I believe to be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writing. This is what I believe to be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reading. And for that reason, I hope this book will help or remind its readers to ‘see’ themselves, and to ‘see’ others.”
Reading this passage, I was suddenly reminded of something I had written down back in middle school when I first read Blindness by José Saramago—something about the act of seeing. At the same time, my mind wandered to Final Fantasy XIV: Dawntrail (7.0) and its themes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different species. To truly understand others requires not just an open and enriched heart, but also deep thought and a wealth of life experience.
写得很好,文字功底极强,行文看下来没有一句多余冗杂的话,文章写起来就像技术高超的外科医生利落精准地完成一场难度很高的手术。单凭陈述性的语句,就能传递震撼人心的感情。尤其是对亲情部分的描写,非常动人。我的感受是,作者擅长写人,更擅长懂人,对他人情感与自尊有着敏锐的洞悉,却又将这些略有刺痛的观察隐藏在了风平浪静的文字里。平静的话语,也可以让细腻的感情悄无声息地潜伏并伺机袭击读者的心灵。当然,作者的阅历和成长环境或许也孕育了他对生死的感悟。每当读到这些淡定却沉重的文章,我的心都会悄悄屏住呼吸几秒,在悲伤之余偶尔也会感慨自己的天真和脆弱。
在讲述母亲和作者担任[一家之主]的故事的时候些许引起了我的不适,一个是作者的男性视角,一个是闽南那视作理所当然的父权环境。还有一些阅读时的观点和不适,我有点忘记了,就不在这里写。
最后一段后记中,作者提到“
“人各有異,這是一種幸運:一個個風格迥異的人,構成了我們所能體會到的豐富的世界。但人本質上又那麼一致,這也是一種幸運:如果有心,便能通過這共通的部分,最終看見彼此,映照出彼此,溫暖彼此。
這是我認為的「寫作的終極意義」,這是我認為的「閱讀的終極意義」。我因此多麼希望,這本書能幫助或提醒讀者,「看見」自己,「看見」更多人。”
我突然想到初中读[失明症漫记]时记下的和「看見」相关的话语,也很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ffxiv 7.0中关于各物种之间相互理解的桥段。理解他人,真是需要开放豊か的心灵的同时,也需要思考与人生的阅历啊。
“知道阿太去世,是在很平常的一個早上。母親打電話給我,說你阿太走了。然後兩邊的人抱著電話一起哭。母親說阿太最後留了一句話給我:「黑狗達不准哭。死不就是腳一蹬的事情嘛,要是誠心想念我,我自然會去看你。因為從此之後,我已經沒有皮囊這個包袱。來去多方便。」
那一刻才明白阿太曾經對我說過的一句話,才明白阿太的生活觀:我們的生命本來多輕盈,都是被這肉體和各種慾望的污濁給拖住。阿太,我記住了。「肉體是拿來用的,不是拿來伺候的。」請一定來看望我。”
“抱怨從姐姐那開始的,「為什麼要亂花錢?」
母親不說話,一直埋頭收拾,我也忍不住了:「明年大學的學費還不知道在哪呢?」
「你怎麼這麼愛面子,考慮過父親的病,考慮過弟弟的學費嗎?」姐姐著急得哭了。
母親沉默了很久,姐姐還在哭,她轉過身來,聲音突然大了:「人活著就是為了一口氣,這口氣比什麼都值得。」這是母親在父親中風後,第一次對我們倆發火。
母親帶我默默上了二樓,進了他們的房間。吃飽飯的父親已經睡著了,還發出那孩子一般的打呼聲。母親打開抽屜,掏出一個盒子,盒子打開,是用絲巾包著的一個紙包。
那是老鼠藥。
在父親的打呼聲中,她平靜地和我說:「你爸生病之後我就買了,好幾次我覺得熬不過去,掏出來,想往菜湯裡加,幾次不甘願,我又放回去了。」
「我還是不甘心,我還是不服氣,我不相信咱們就不能好起來。」
母親很緊張地用力地捏著那卷錢,臉上憋成了紅色,像是戰場上在做最後攻堅宣言的將軍。「這附近沒有人建到四樓,我們建到了,就真的站起來了。」
我才知道,母親比我想像的還要倔強,還要傲氣。
我知道我不能說不。
果然,房子建到第四層後,小鎮一片嘩然。建成的第一天,落成的鞭炮一放,母親特意扶著父親到市場裡去走一圈。”
“母親很緊張地用力地捏著那卷錢,臉上憋成了紅色,像是戰場上在做最後攻堅宣言的將軍。「這附近沒有人建到四樓,我們建到了,就真的站起來了。」
我才知道,母親比我想像的還要倔強,還要傲氣。
我知道我不能說不。
果然,房子建到第四層後,小鎮一片嘩然。建成的第一天,落成的鞭炮一放,母親特意扶著父親到市場裡去走一圈。
就像生態魚缸裡的珊瑚礁,安放在箱底,為那群斑斕的魚做安靜陪襯,誰也不會在意渺小但同樣驚心動魄的死亡和傳承。
父親火化後第二天,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他不滿地問我,為什麼只燒給他小汽車,沒給摩托車,「我又不會開小汽車」,夢裡他氣呼呼地說。
醒來告訴母親,不想,她說她也夢到了。夢裡父親著急地催著:他打算自己騎摩托車到海邊去逛逛,所以要趕緊給他。
「你那可愛的父親。」母親笑著說。
他會如願的。颱風就是這樣,來之前一點聲息都沒有,到來的時候就鋪天蓋地。
先是一陣安靜,然後風開始在打轉,裹著沙塵,像在跳舞,然後,突然間,暴風雨在下午一點多,槍林彈雨一般,呼嘯著到來了。我看見,路上的土地被細密地砸出一個個小洞,電視裡那記者,也如願地開始站在風中嘶吼著報道。
我一個人默默搭著電梯,走到樓下。燃放煙花的痕跡還在那,灰灰的,像一層淡淡的紗。
我知道過不了幾天,風一吹,沙子一埋,這痕跡也會不見的。
一切輕薄得,好像從來沒發生過。
醫院一樓是門診大廳和停屍房。可以隨意打發的疾病,和已經被疾病廢棄的身體,比鄰而居。生和死同時在這層盛放。
她在投入地奔忙著,我則不知所措地整天在街上晃蕩。因為一回家,就會真切地感知到,似乎哪裡缺了什麼。這樣的感覺,不激烈、不明顯,只是淡淡的,像某種味道。只是任它悄悄地堆積著,滋長著,會覺得心裡沉沉的、悶悶的,像是消化不良一般,我知道,這可能就是所謂的悲傷。
“每一種困難,都有神靈可以和你分擔、商量。」母親就此願意相信有神靈了,「發覺了世界上有我一個人承擔不了的東西,才覺得有神靈真挺好的。
人流分開了,她的母親顫顫悠悠地走出來,對著樓上的張美麗,哭著喊:「你就是妖孽啊,你為什麼那時候就不死了算了,你為什麼要留下來禍害……」
擴音器旁的張美麗估計很久沒看到母親了,哭著喊:「媽,你要相信我,我對天發誓,我從以前到現在從沒做過傷天害理的事情,我真的從來沒有。」
她的母親顯然已經崩潰了:「你就是妖孽,你就是妖孽,我當時應該掐死你。”
“那個晚上我沒聽到聲響,是第二天醒來後才知道的。張美麗當晚跪在自己宗族的祠堂門口,大聲哭著,對天發誓自己沒有作孽,「除了一開始追求愛情,我沒有做娼妓,沒有賣毒品,我只是把我覺得美的、對的、我喜歡的,都做成生意,我真沒有作孽……」
哭完,她狠狠地往祠堂的牆撞去。
第二天祠堂大佬起來才看到,張美麗死在祠堂的門口,流出來的血都凝結了,像沉壓已久的香灰。
我一聲不吭,拿著酒走到一個角落,剛好看到那片綠地。我反覆想起,那石頭房子,那蒼白的臉。「她終究是個小鎮姑娘,要不她不會自殺的。」我對自己說。
同學們還在起哄,說著這地方曾經淫蕩的種種傳說。
我突然心頭衝上一股怒火,把酒杯狠狠往地上一摔,衝出去,一路狂跑,一直狂跑,直到我再也看不見那個噁心的娛樂城。
在帶上她辦公室門的時候,我忍不住轉頭想再看她一眼,卻一不小心看到,她像突然洩氣一般,後腦勺靠在座椅背上,整個人平鋪在那老闆椅上,說不出的蒼老和憔悴。
我看著這樣的他,越發覺得遙遠。我知道他身上流動著一種慾望,一種強烈而可怕的慾望。他要馬上城市起來,馬上香港起來。他要像他想像裡的香港人那樣生活。
我看著老家的阿小,躲在香港阿小背後,跟著一臉的賠笑。我說不出的難受,說,算了,我不玩了。轉頭就走。
從此,即使阿月姨叫我再去幫忙補習,我都借口推了。
我害怕看到老家阿小的這個樣子,他會卑微到,讓我想起自己身上的卑微。
打漁要趕早潮,每天早上五六點,我就聽到那摩托車帥氣地呼呼地催引擎,發出的聲音,炫耀地在小巷裡擴散開。他每天就這樣載著父親,先去下海布網。他大哥和二哥,則踩著那輛吭哧吭哧響的自行車跟在後頭。
下午三四點他們就打漁結束回來了。海土、海風和直直炙烤著他們的太陽,讓他越來越黝黑。每次把滿裝海鮮的籮筐往家裡一放,他的油門一催,就呼嘯著玩耍去了。沒有人知道他去哪,但是後來很多人常告訴我,看到阿小,沿著海岸線邊的公路,以超過時速一百的速度瘋一樣地呼嘯而過,嘴裡喊著亢奮的聲音。
慢慢地,我注意到他留起了長頭髮,每次他開摩托車經過我家門口,我總在想,他是在努力成為香港阿小想成為的那個人嗎?
他的字還是那麼差,扭扭捏捏,但已經換成繁體字了:
親愛的黑狗達!
好久不見。
我在香港一切很好。香港很漂亮,高樓大廈很多,有空來找我玩。
衹是我不太會說粵語,朋友不太好交,多和我來信吧,我找不到一個人說話。
我家換了地址,請把信寄到如下……
我知道他在香港可能一切都很不好。我突然想像,在那個都是白襯衫、白牙齒的教室裡,另外一群孩子高傲地看著他,悄悄地在他背後說鄉巴佬。
我莫名其妙地難過。
拿著信,我去敲了烏惜家的門。這個阿小正在自己玩吉他。當時流行的一部香港電視劇裡,主人公總在彈吉他,許多潮流男女都在學。
我拿出香港阿小的信給他看。
他愣住了,沒接過去。
「他給你寫信?」
我明白了,香港阿小沒給他寫信。
這個阿小搶過信,往旁邊的爐子一扔。香港阿小的信,以及回信的地址就這麼被燒了。
高三的後半學期,整個學校像傳銷公司。
老師整天說,別想著玩,想想未來住在大城市裡,行走在高樓大廈間,那裡才好玩。他們偶爾還會舉例:某某同學,考上了北京的大學,然後,他就住在北京了……
口氣篤定得好似王子和公主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
誰都沒懷疑住在北京就是所有幸福的終點。整個高三的年段,也像是準備離開小鎮的預備營地,許多人開始寄宿在學校,全心投入一種冥想狀態。彷彿學校就是一艘太空船,開往一個更開明的所在。
他望著窗外的橋,像自言自語一樣:「我來香港第三年,父親查出來得了癌症,鼻咽癌,建築公司不得不停了,父親到處找醫院醫病,本來還有希望,結果哥哥怕被拖累,捲著家裡的錢跑了。我和母親只好賣掉房子,繼續給父親醫病。有一天,他自己開著車來到這裡,就從這裡衝下去了。我現在要掙口飯吃,還要從這經過。」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麼接話。
他接著自言自語:「城市很噁心的,我爸一病,什麼朋友都沒有了。他去世的時候,葬禮只有我和母親。」
「呵呵。」停頓了一會兒後,他自己輕輕笑了一下。
我張了張口,嘗試說點什麼。他顯然感覺到了。
“我沒事的,其實可搞了,香港報紙還有報道這個事情,我家裡保留著當天的報紙,是頭版頭條,你相信嗎?」他轉過頭來,還是微笑著的臉,但臉上早已經全是淚水。
車依然在開,那座橋漫長得似乎沒有盡頭。橋上一點一點的燈影,快速滑過,一明一滅,掩映著車裡晃動著的疲倦人群。
大部分人都睏倦到睡著了——他們都是一早七點準時在家門口等著這車到市區,他們出發前各自化妝、精心穿著,等著到這城市的各個角落,扮演起維修工、洗碗工、電器行銷售、美發店小弟……時間一到,又倉皇地一路小跑趕這趟車,搭一兩個小時回所謂的家,準備第二天的演出。
他們都是這城市的組成部分。而這城市,曾經是我們在小鎮以為的,最美的天堂。他們是我們曾經認為的,活在天堂里的人.
那天我終於沒勇氣問他,如何和大城市同學的譏諷相處。事實上,那天之後,我突然很不願意再和他聊天了。和他說話,就如同和一個人在水裡糾纏,你拉著他,想和他一起透口氣,他卻拉著你要一起往下墜。
“雖然有許多擔心和好奇,但我終究沒再去敲他家的門。我心裡隱隱覺得,他的腦子或者心裡有種異樣的東西,說不上那是不是病,但我害怕自己會被傳染上。
我害怕哪一天我會憎恨生養我的小鎮,會厭惡促成、構成我本身的親友。
我想,或許他代表了我們這種小鎮出生的人,某種純粹的東西。那種東西,當然我身上也有。我在想,或許他是某部分的我。
要感謝文展的是,我基本不太想太長遠的事情,很多事情想大了會壓得自己難受。我只想著做好一點點的事情,然後期待,這麼一點點事,或許哪天能累積成一個不錯的景觀。起碼是自己喜歡的景觀。
在他們極度亢奮的時候,總是不自覺把聲音抬高,那聲音,總有幾個音節讓我回想起文展那因為兔唇而顯得奇特的腔調,再定睛一看,我總能找到他們臉上和文展類似的部分。我會突然想,在這麼密密麻麻的人群中,那個兔唇、倔強的文展,究竟處在哪種生活中。
邊往上走,我邊想像,如果是文展,他此時是否會覺得豪氣萬丈,未來就這麼鋪展在眼前。我想到的,倒一直是對生活的不確定,我享受一個城市提供的更好的平台,但我不知道自己終究會比較享受怎麼樣的生活。
爬到景山公園最高處,我突然想給文展打電話。他的母親每次過年,總是要來找我聊聊天,然後一次次抄寫給我文展的號碼。她說:「你有空和他聊聊吧。」我知道,文展的母親心裡還是隱隱地不安。但她不敢把這不安說出口,似乎一說出口,一切就清晰可見,一切擔心就落地為實了。
電話接通了。「哪個兄弟啊?有什麼好事找啊?」他的聲音竟然聽不出兔唇的感覺。他再次吞下了自己的殘疾,但是,不是以童年時期的那個方式。
在啟程回老家前的一個月,我竟然不斷想像,和文展相見會是如何的場景。我不斷在思考,自己是該客氣地和他握手,還是如同以往,像個哥們兒拉住他擁抱一下。
但我們已經十幾年沒見了。十幾年,一個人身上的全部細胞都代謝完多少輪。我因而又惴惴不安起來。
“我們又沉默了許久。他似乎意識到我努力背後的善意,試圖挑起話題:「我在廣播站,還播過你的文章。」
「是你特意關注的嗎?哈,我又不是什麼大作者。」我馬上抓住機會,試圖通過自嘲,讓這個對話進入放鬆的階段。
然後我開始講述,自己在外地生活的種種。
我沒有預料到,他竟然沉默了。而且這一沉默,不像我想像的,只是一個小小的、可以逾越、可以熬過的間歇。他冷漠地坐在那,任由沉默如同洪水汩汩淌來,一層層鋪來,慢慢要把人給吞沒了。
我終於忍不住,站起身說:「那打擾了,我先回家了。」
此刻他卻突然說話了:「對不起,其實我也說不清楚,自己為什麼厭惡你。”
“我愣住了。
「你說,憑什麼是你?為什麼不是我?」
我知道他在說的是什麼,我知道他提問的,是我們都沒辦法回答的問題。
第二天,我改了機票提前回北京。在路上,我反覆在想,自己此前對文展耿耿於懷的原因,是因為我有種無意識的愧疚感,彷彿我莫名其妙地過了他應該過的生活?又或許,是因為,我知道,從本質意義上,我們都是,既失去家鄉又永遠沒辦法抵達遠方的人。”
我因此覺得莫名其妙的崇拜——文展是我見過的唯一一個降伏了缺陷的孩子。
我才明白,那封信裡,我向文展說的「小時候的玩伴真該一起聚聚了」,真是個天真的提議。每個人都已經過上不同的生活,不同的生活讓許多人在這個時空裡沒法相處在共同的狀態中,除非等彼此都老了,年邁再次抹去其他,構成我們每個人最重要的標誌,或許那時候的聚會才能成真。
我知道,他和我這輩子都注定無處安身。
從一家雜誌社的試用機會開始,我得到了進入這個城市的機會,或者也可以說,得到被這個城市一口吞沒的機會。
在一段時間裡,我覺得這個城市裡的很多人都長得像螞蟻:巨大的腦袋裝著一個個龐大的夢想,用和這個夢想不匹配的瘦小身軀扛著,到處奔走在一個個嘗試裡。而我也在不自覺中成為了其中一員.
他不是假裝,他只不過不知道怎麼處理自己身上的各種渴求,只是找不到和他熱愛的這個世界相處的辦法。每個人身上都有太多相互衝突卻又渾然一體的想法,他只是幼稚,還沒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誰。」打好的這條短信我最終沒發出去,因為覺得,沒有必要向她解釋什麼。因為,她也是個不知道自己是誰的人。
不想哭,內心憋悶得難受,只能在租住的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間裡,不斷來來回回地到處走,然後不斷深深地、長長地歎氣。彷彿我的胸口淤積著一個發酵出濃郁沼氣的沼澤,淤積著一個被人拚命咀嚼,但終究沒能被消化,黏糊成一團的整個世界。
也就是在那時候,我突然察覺,或許我也是個來北京看病的人。
或許,我和厚樸生的是同一種病。
我不知道他哪句是真話,生存現實和自我期待的差距太大,容易讓人會開發出不同的想像來安放自己。我相信,他腦子裡藏著另外一個世界,很多人腦子裡都偷偷藏著很多個世界。
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大概以為自己是馬丁·路德·金。「多麼貧瘠的想像力,連想像的樣本都是中學課本裡的。」我在心裡這樣嘲笑著。
我沒有直接反駁他,也許,我也在隱隱約約期待著,有人真可以用務虛的方式,活出我想像之外更好的人生。
我喜歡這樣的厚樸,我也願意相信這樣的厚樸,但我總覺得他是在為所有人的幻象燃燒生命。假如這個幻象破滅,別人只是會失望,但厚樸自己的內心會發生什麼呢?
在我看來,厚樸和王子怡的戀情非常容易理解:厚樸以為通過擁有王子怡可以證明自己又突破了什麼,而王子怡以為通過厚樸完成了對自我所擁有的一切的反叛。其實王子怡才是比厚樸更徹底的反叛者,或者說,來神遊閣的其他人,其實都比厚樸更知道自由的世界是什麼。
無論如何,這段戀情確實揭發了厚樸。自從王子怡搬到神遊閣後,來的人就少了。那些人以為自己不願意來的原因是因為這個「來自舊世界」的王子怡,以為王子怡身上老土的腐朽感污染了自由世界,但或許他們心裡清楚,他們只不過是察覺到了厚樸身上的另一個部分。
他告訴我,原來的樂隊散了,誰被父母拉去實習了;誰準備考研了;誰認真地開始籌備畢業論文,希望衝擊優秀畢業生,爭取選調到政府部門……他們的「世界樂隊」,現在看來,更像是以青春的名義集體撒的一個嬌。在看到現實的未來後,各自投奔到新的軌跡裡去了,還賦予這樣的行動另外一個名字:追求。
我瘋狂工作,不讓自己有空餘時間,除了真實的生存壓力,還在於,我根本不敢讓自己有空餘的時間,因為時間一空下來,我就要回答怎麼去填充時間,怎麼去面對生活,去回答這個問題——我要怎麼生活,我真正喜歡的是什麼,我真正享受什麼?
或許,生活就是張這樣的問卷,你沒有回答,它會一直追問下去,而且你不回答這個問題,就永遠看不到下一個問題。
原諒我,父親,從你生病開始我就一直忙於在外面兼職賺錢,以為這樣就能讓你幸福,但當我看到我給你的唯一一張照片,被你摸到都已經發白的時候,才知道自己恰恰剝奪了我所能給你的、最好的東西。
在祖父祖母的墓地,這些與你血脈相連的宗親跟著不變的禮儀祭拜完,也各自散坐在這高台上,像是一起坐在祖宗的環抱中,共同圍繞著這個埋葬著祖宗的塚。
那一刻我會覺得自己是切開的木頭年輪中的某一個環,擁擠得那麼心安。
我知道那種舒服,我認識這裡的每塊石頭,這裡的每塊石頭也認識我;我知道這裡的每個角落,怎麼被歲月堆積成現在這樣的光景,這裡的每個角落也知道我,如何被時間滋長出這樣的模樣。
我生平一定曾路過
你洗過澡的那條河
你的六歲
還浮游在水面
我抬起頭
看到一個碩大的
橘子
懸在上空
我知道
這就是童年時代的
所有黃昏
——《關於所有旅行的故事》
作為遊客,愜意的是,任何東西快速地滑過,因為一切都是輕巧、美好的,但這種快意是有罪惡的。快速的一切都可以成為風景,無論對當事者多麼驚心動魄。
九年前,坐在這位置上的我,父親半身偏癱,是家境困頓到無路可去的時候。當時那個蔡崇達,想著的是如何掙錢送父親到美國治病,可以為了考慮是否為整天兼職而辛苦的自己加一塊紅燒肉而猶豫半天,還立志多掙點錢帶阿太去旅遊,當然還想著要趕緊牛起來,趕緊出名,讓給自己機會的當時廣電報的老總王成剛驕傲。甚至曾經想像,在哪一本書暢銷後,要回到父親做心臟手術的福二院,對那些病患的子女講,別放棄,生活還有希望。
九年後,那個當年的蔡崇達執著的理由全部消失,父親、阿太、成剛的突然離世,讓他覺得自己突然輕盈得無法觸碰到真實的土地。而他唯一找到的辦法,就是拚命工作。
這幾年來我就這樣生活在兩個世界的夾縫中.
時光多殘忍,那個懦弱但可愛的父親,兢兢業業一輩子的所有印記一點都不剩下;那個過於狂熱、戰天斗地的兄長成剛,短暫地燃燒生命,也就耀眼那一瞬間;而我深愛著的、那個石頭一樣堅硬的阿太,還是被輕易地抹去。太多人的一生,被抹除得這麼迅速、乾淨。他們被時光拋下列車,迅速得看不到一點蹤影,我找不到他們的一點氣息,甚至讓我憑弔的地方也沒有。
而對於還在那列車中的我,再怎麼聲嘶力竭都沒用。其中好幾次,我真想打破那個玻璃,停下來,親吻那個我想親吻的人,擁抱著那些我不願意離開的人。但我如何地反抗,一切都是徒然。
我才明白,我此前並不是接受旅遊這種生活方式,我那只是逃避。雖然我反覆告訴自己,既然人生真是個旅途,就要學會看風景的心情和能力。
說實話我一直不理解,也一直像個任性的孩子接受不了,為什麼時光這列車一定要開得這麼快,為什麼還要有各自那麼多分岔,我不知道我們這麼急匆匆地到底要去向何方?但我知道,或許不僅是我一個人在大呼小叫,那些靜默的人,內心裡肯定和我一樣地潮汐,我不相信成熟能讓我們接受任何東西,成熟只是讓我們更能自欺欺人。其實那次我旅遊完回來,寫了另外一首詩叫《世界》:
世界都不大
我可以哪裡都不去
我可以在這裡
只看著你
直到一切老去
“很幼稚的詩,但我很驕傲,即使過了九年,我依然如此幼稚。這是幼稚的我幼稚的反抗。原諒我這麼感傷,那是因為,不僅是過去、現在的我,多想挽留住自己最珍惜的東西,卻一次次無能為力。但我還是願意,這麼孩子氣地倔強抗爭,我多麼希望能和我珍惜的人一直一路同行,但我也明白,我現在唯一能努力的是,即使彼此錯身了,我希望,至少我們都是彼此曾經最美的風景——這也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反抗。
我常對朋友說,理解是對他人最大的善舉。當你坐在一個人面前,聽他開口說話,看得到各種複雜、精密的境況和命運,如何最終雕刻出這樣的性格、思想、做法、長相,這才是理解。而有了這樣的眼睛,你才算真正「看見」那個人,也才會發覺,這世界最美的風景,是一個個活出各自模樣和體系的人。
顯然,我沒能「看見」我的父親,也已經來不及這樣去看父親了,他已從我的生活中退場。我開始擔心,自己會以這樣的方式,錯過更多的人。這惶恐,猶如一種根本的意識,就這麼植入了內心。
也是從那篇文章開始,生發出一種緊迫感:我應該看見更多的人。這是對路過生命的所有人最好的尊重,這也是和時間抗衡、試圖挽留住每個人唯一可行的努力。還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路過我們生命的每個人,都參與了我們,並最終構成了我們本身。
也從那時候開始,寫這本書,就不僅僅是「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了,而是「必須做的事情」了——我在那時候才恍惚明白寫作的意義——寫作不僅僅是種技能,是表達,而更是讓自己和他人「看見」更多人、看見「世界」的更多可能、讓每個人的人生體驗盡可能完整的路徑。
然而當我真正動筆時,才發覺,這無疑像一個醫生,最終把手術刀劃向自己。寫別人時,可以模擬對象的痛感,但最終不用承擔。而在寫這本書時,每一筆每一刀的痛楚,都可以通過我敲打的一個字句,直接、完整地傳達到我的內心。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或許這才是寫作真正的感覺。也才理解,為什麼許多作家的第一本都是從自己和自己在乎的部分寫起:或許只有當一個寫作者,徹徹底底地解剖過自我一次,他書寫起其他每個肉體,才會足夠的尊敬和理解。
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有一些文章就像是從自己的骨頭裡摳出來的。那些因為太過在乎、太過珍貴,而被自己刻在骨頭裡的故事,最終通過文字,一點點重新被「拓」出來,呈現出當時的樣子和感受。
人各有異,這是一種幸運:一個個風格迥異的人,構成了我們所能體會到的豐富的世界。但人本質上又那麼一致,這也是一種幸運:如果有心,便能通過這共通的部分,最終看見彼此,映照出彼此,溫暖彼此。
這是我認為的「寫作的終極意義」,這是我認為的「閱讀的終極意義」。我因此多麼希望,這本書能幫助或提醒讀者,「看見」自己,「看見」更多人。